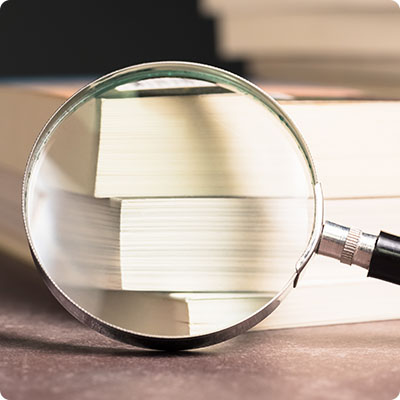传说中的建筑
大津巴布韦国家纪念碑无疑是该国最著名的景点。这座中世纪城市曾在 1100 年至 1450 年间繁荣一时,是庞大的绍纳帝国的首都。非洲最伟大的文明之一(仅次于法老文明)就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许多人将其称为 "石头文明"。津巴布韦一词本身的意思就是 "石头的房子"。绍纳人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加工石头的技术:他们把石头浸泡在非常热的火中,然后浇上水,使石头更容易切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使用灰泥也能做出高质量的接缝。因此,厚重的墙壁具有完美的形状和光滑的墙面。为了确保整体的稳定性,绍纳人有时会选择底座较宽而顶部逐渐变细的结构。大津巴布韦遗址由三个主要区域组成。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居住在上城,令人印象深刻的花岗岩城墙将两个不同的围墙隔开,由一系列狭窄的通道连接,其中一些通道是有顶的。西边的围墙是王室的住所,而东边的围墙则是遗址中最神圣的部分。请留意六根顶部雕有鸟类的大型皂石柱子。这些雕刻的鸟类已成为国家的象征,是人与神之间的信使。卫城下面是大围墙。它的平面呈椭圆形,里面有一系列被称为 "达加"的土坯房(由花岗岩砂和粘土混合而成)、一个由通道连接到一个令人惊叹的锥形塔的公共区域,以及多个由石墙分隔的家庭区域,一般由围绕庭院布置的两间小屋和一个厨房组成。这个大型围墙似乎是为安置国王的各种妻子而设计的。王公贵族们被集中在山谷建筑群中,在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用干石墙隔开的土坯房,这些土坯房展示了精湛的装饰工艺,特别是人字形和棋盘式图案。
大津巴布韦遗址展示了建筑作为自然环境延伸的理念,而卡米遗址则见证了旨在塑造和改造环境的建筑的出现。卡米曾是布图瓦王国的首都,由托尔瓦的绍纳王朝统治,在16世纪取代了大津巴布韦。这两个遗址有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在空间组织方面。酋长府邸(曼波)矗立在山丘上,俯瞰着被花岗岩围墙环绕的土坯小屋,而众多的通道和有顶长廊则将不同的区域连接起来。干砌石墙的技术仍在使用,但这次墙壁不再只是用来划分空间,还用来塑造空间。卡米遗址引入了挡土墙的概念,从而创造出一系列复杂的平台和露台。作为关键的建筑元素,这些墙壁一直是装饰的焦点。在离格韦鲁镇不远的纳莱塔勒 Dzimbabwe 建筑群中,可以看到这种丰富的装饰效果,该建筑群兴盛于16世纪至18世纪。纳莱塔勒是中心遗址,其椭圆形城墙直径达 60 米,装饰丰富,有楔形、绳形、棋盘形、双楔形图案和彩色石块镶嵌。它周围还有一些卫星遗址,如恩萨兰萨拉(Nsalansala),其独特之处在于城墙内外都有装饰。当时葡萄牙人在此的遗迹已所剩无几。在丹巴拉雷、马萨佩和卢安泽,仍可看到由土墙和壕沟环绕的砖砌防御工事。葡萄牙人还在这里建立了传教会,并以砖砌教堂为中心。
方言财富
在保护性植物围栏的包围下,圆顶形的桑族人的小屋由细枝框架组成,上面铺设了草和芦苇。这种在简单而实用的建筑中使用天然和当地材料的愿望在整个传统农村建筑中都可以找到。大多数村庄由围绕中央社区空间的圆形小屋组成。每个小屋都有特定的功能(做饭、洗衣、睡觉等)。这些小屋可能是在树枝或晒干的砖的框架上用泥土或粘土砌成的,最常见的是有一个锥形的茅草屋顶。今天,圆形小屋和带波纹铁皮屋顶的长方形混凝土房屋并排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少见。储藏室仍然由天然材料制成。许多粮仓都建在高跷上,以保护粮食。当农业生产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田地附近建有高架结构,供工人居住。这些村庄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牛栏或Kraal。这个源自南非荷兰语的词最初指的是圆形村庄,按照非常严格的空间和社会等级制度组织起来,并由棕榈树一样的荆棘堡垒保护。在恩德贝勒人中,某些村落被称为 "皇家"。它们呈椭圆形,周围有坚固的柱子组成的栅栏,具有军事和战略性质。但是,如果说今天的恩德贝勒人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传统居住地的丰富形式和色彩。男人们负责建筑:木制框架、茅草屋顶、粘土和泥墙。房子通常是长方形的,前面有一个院子,有一个保护性的围墙。外面有一个房间,是一种小亭子,专门用来做饭和洗衣。妇女们负责装饰,也就是房屋的身份。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妇女们主要用天然颜料工作,产生棕色或赭石色,但也用煤灰和白石灰来画黑白的线条和图案。随着丙烯酸和乙烯基涂料的发现,房屋被装饰成明亮的颜色。起初,只有几何图案受到青睐,后来妇女们逐渐加入了形象元素。作为身份的象征,这些壁画长期以来也被用来表达对恩德贝勒人遭受的各种压迫的文化抵抗。
殖民时代
哈拉雷市和布拉瓦约市仍保留着典型的殖民时期城市布局。布拉瓦约在创建之初就有了宽阔的大道,以便牛车在路口进行 90 度转弯。在建筑方面,兼收并蓄是当时的主流。布拉瓦约的圣母无原罪大教堂(Basilica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采用了伟大的哥特式风格,尖拱和细长的圆柱通向一个非常高的天花板,天花板上覆盖着令人惊叹的木质框架。位于哈拉雷的圣心大教堂则完全采用了哥特式罗马风格,塔楼上饰有尖顶,窗户上镶有长方形花窗,显得庄严肃穆。与哈拉雷的绿地和植物园一样,这是一种非常维多利亚式的复兴风格。另一方面,官方建筑则更多地采用新文艺复兴风格的门廊和拱廊,或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沉稳、对称的线条。爱德华时代的古典主义风格在市政厅和其他民用 "宫殿 "中大行其道,这些建筑的顶部都有花台和栏杆,外墙则以圆柱点缀。这种风格也出现在酒店中,如维多利亚瀑布酒店,它是帝国建筑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拥有耀眼的白色墙壁。这与豹岩酒店(Leopard Rock Hotel)的粉红色调大相径庭,该酒店拥有城堡般的石基、炮塔和带有优雅栏杆的大楼梯,曾俘获伊丽莎白女王的芳心!在这股历史主义浪潮的同时,一种新型的工程建筑也在发展,市场、火车站和其他文化中心都采用了开放式设计,通过金属框架支撑的玻璃结构沐浴在自然光中。位于哈拉雷的美丽的国家美术馆尤其如此。在住房方面,无论是富丽堂皇的城镇住宅,还是种植园中心的大房子,都反映出欧洲的建筑规范适应了当地气候的实际情况:在装饰方面,它们交替使用南非开普荷兰风格(弧形屋檐、粉刷墙壁、茅草屋顶)、新古典主义风格(圆柱、花饰)和维多利亚复兴风格。采矿和工业活动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开垦了灌木丛,灌溉了干旱的土地,修建了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 卡里巴湖上的大坝高 128 米,长 579 米,有双拱形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水库之一。另一项技术壮举是横跨萨比河的比尔切诺大桥。在 330 米长的跨度上分布着 1500 吨钢材,令人印象深刻。原住民被送往部落托管地,那里是荒凉的地区,没有基础设施,住房岌岌可危,而 "白人 "则在绿树成荫的住宅区和其他高档住宅区繁衍生息。哈拉雷别致的郊区还保留着英国名字(Avondale、Belgravia......)。这就解释了居民与殖民遗产之间的艰难关系。
自1980年以来
津巴布韦独立后,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尤其是在首都。但住房的缺乏导致棚户区激增。但新政府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象征权力的宏伟建筑提供资金。首先是国家英雄广场(National Heroes Acre),这是一个集会和纪念场所。弧形花岗岩护墙的梯田上装饰着人字形图案、铜制的津巴布韦鸟类模型、几何形状和体量--一切设计都让人想起 "石头文明 "的伟大时代。这种对传统的回归真正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政府正努力巩固其权力。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座塔楼的抛光花岗岩墙壁上镌刻着津巴布韦农村的图案,是仿照绍纳文化中的锥形屋顶谷仓建造的。这些粮仓底部宽阔,顶部逐渐变小,可以在干旱时期储存粮食。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是哈拉雷新机场航站楼,其窗户呈人字形水平排列,控制塔让人联想到大津巴布韦的锥形塔,其外部走廊则让人联想到该国伟大石器遗址的有顶通道。这些宏伟的成就并没有掩盖与人口爆炸相关的问题。在哈拉雷,棚户区不断扩大。2005 年,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决定彻底拆除这些棚户区,使数十万人流落街头,或被迫住进临时营地,成为一种新的棚户区。直到 2010 年,哈拉雷棚户区改造项目才重见天日。第一个进行改造的是 Dzivarasekwa。居民们接受了管道和砌筑方面的培训,帮助建造房屋、安装卫生设施、铺设道路,还引入了垃圾分类和太阳能照明等生态解决方案。如今,许多项目已经不再是毫无灵魂的混凝土和玻璃结构,而是提供了一种原始和创新的建筑方法,例如东门中心(Eastgate Center)。由迈克-皮尔斯(Mike Pearce)设计的这座购物中心是仿生物建筑的完美典范。它以白蚁丘为模型,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小孔,以确保持续的自然通风和稳定的气候。该建筑具有生态效益,不使用空调,能耗降低了 90%。另一项杰出成就是马蓬古布韦公园讲解中心。该中心由彼得-里奇(Peter Rich)设计,其穹顶和拱门均由当地石材覆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津巴布韦,创新似乎常常与朴实无华相呼应,位于哈拉雷霍普利(Hopley)的 "新星学校"(Rising Star School)就证明了这一点。当地石匠在没有使用先进技术工具、没有永久性水电供应的情况下铺设了 600 000 块砖......这是一项真正的壮举!其他当代建筑还包括阿伯福伊尔美丽的拱形画廊,其弧形屋顶、檐窗和悬挑阳台可将全景尽收眼底;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戈塔大坝住宅,这是一座悬挑在岩石上的宏伟别墅,其花岗岩、木材和玻璃体量仿佛漂浮在水库水面上。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