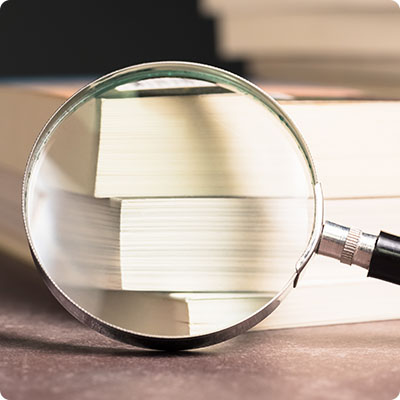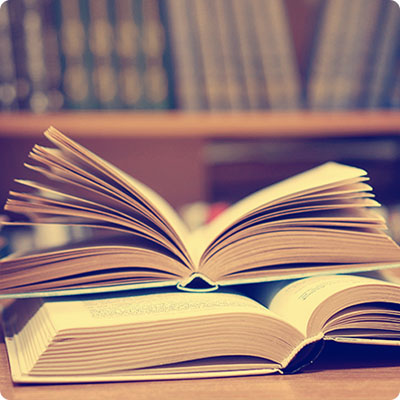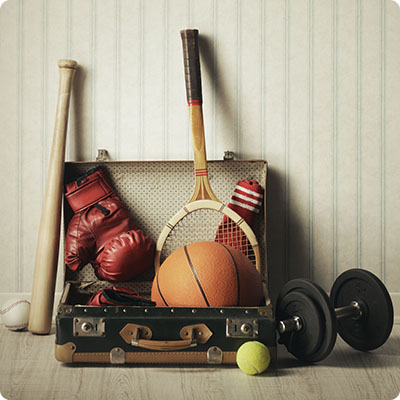巴林
今天,波斯湾的阿拉伯城市是21世纪全球化社会名副其实的展示窗口:整个地球都被资本主义的耀眼光芒所吸引,聚集在这里。但与邻国阿联酋不同的是,巴林成功地保留了强大的本地人口:超过 45% 的人口是巴林人,而在迪拜或卡塔尔,超过 87% 的居民是外国人。这在本地区确实是一个反常现象,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
国家优先
长期以来,巴林王国的人口多于海湾邻国,因此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较少,而在20世纪,由于碳氢化合物带来的经济甘露,世界的这一地区得到了飞速发展。因此,巴林国努力向本国公民倾斜。例如,根据法律规定,一家公司至少有一半的员工必须是巴林人。这种民族偏好如今已初见成效。在迪拜,游客可能永远不会遇到阿联酋人,但在巴林群岛,巴林人却随处可见。巴林人比阿联酋人更多,但他们获得的国家补贴较少,因此没有同样的经济机会。他们从事着邻居们早已放弃的职业,如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和渔民。
巴林仅有 150 多万居民,是阿拉伯世界中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其人口密度却是该地区最高的国家之一。近 9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主要集中在首都和群岛主岛上的邻近城镇。城市人口的集中加强了社区之间的反差,使本已复杂的社会动态更加突出。
复杂的阿拉伯-波斯社会
但不要误会,巴林人口本身比你想象的更加多样化。70% 的巴林人是什叶派,而他们本身又分为两个不同的族群。首先是巴哈纳人,他们占巴林什叶派的大多数,是巴林古老历史的继承者。他们是闪米特人,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信奉什叶派。阿贾姆人是19世纪来到巴林的波斯移民的后裔。他们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和语言--波斯语,并在家中使用。逊尼派占群岛穆斯林的 30%,他们来自阿拉伯半岛,在 1783 年埃米尔法提赫征服巴林岛时追随他。这些沙漠贝都因人是居住在沙特阿拉伯东海岸的部落的后裔,以畜牧业、渔业、贸易和多次袭击商队为生。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分为氏族和部落,至今依然存在。因此,世袭王权与王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密不可分,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将统治家族与国家割裂开来。但贝都因人并非巴林唯一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不能与从非洲之角移民到巴林的非洲裔阿拉伯人混为一谈,也不能与19世纪离开故土到巴林工作的伊朗逊尼派乌瓦拉人混为一谈。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民族和宗教混合体一直相对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语言和多重身份
王国语言的多样性反映了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也是公共领域最常用的语言。它是波斯湾地区特有的方言阿拉伯语,来自黎凡特或马格里布的人不一定能听懂。文学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但在麦纳麦街头还能听到其他几种语言。英语是教育和商业语言,在公司、行政机构和公立学校无处不在。大多数巴林人都会说英语,至少足以让人听懂。阿贾姆人社区仍然讲波斯语,尽管波斯语的使用越来越少。但在麦纳麦街头,主要是在老城区,游客会听到来自印度次大陆的语言,主要是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这种语言多样性反映出该国是一个本地传统与外来影响并存的群岛国家。
宗教和种族大熔炉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贸易吸引了大量印度和波斯人来到这个群岛,这也是大量移民工人涌入的原因。麦纳麦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王国的发展潜力也吸引了大量资本和投资者。外国人无法享受与本地人相同的法律。这种现状解释了本地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相对社会鸿沟。居住在巴林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印度次大陆,即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其他主要群体包括菲律宾人和埃及人。这些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有助于维持群岛的经济发展:他们一般在酒店和餐馆从事低技能工作。西方侨民,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石油天然气和银行等关键部门工作。巴林还是海湾地区唯一的犹太社区。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一些动乱,但该社区成员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与穆斯林同胞和谐相处。其中一位名叫 Houda Nonoo 的犹太人甚至成为了上议院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