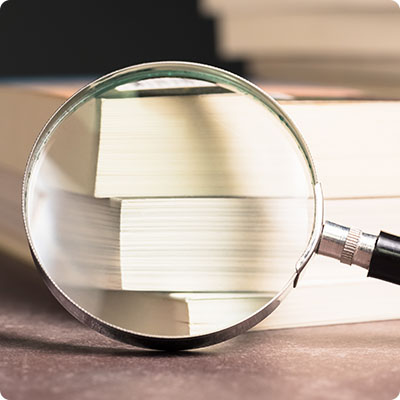黄金时代
他出生的确切年份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毫无疑问是在15世纪下半叶初,当时的欧洲并不缺乏书籍,但拉丁语仍是学习的语言,对于那些或多或少被迫加入教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伊拉斯谟是私生子,但他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鹿特丹到古达(他的家庭在他青年时期定居于此),从巴黎(他在索邦大学就读并结识了意大利诗人福斯特-安德烈林)到英格兰(他在那里与《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成为朋友)。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孩子,也是一位优秀的古人鉴赏家,他喜欢旅行,热衷于与各种国际友人通信,这激发了他的灵感,使他成为世界主义的倡导者之一(根据他的座右铭:"整个世界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园"),这只是他人文主义的一个方面,因为他倡导和平,批评神职人员忘记了福音书的信息。他最有名的作品是 《赞美疯狂》(Élogede la folie)(1511 年),这是一部嘲讽娱乐和哲学手册,其中同名的女神向人类讲话,批评他们的失败。据说这部作品甚至让教皇利奥十世都捧腹大笑,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作者于 1536 年 7 月 12 日在巴塞尔去世后被列入黑名单。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迪尔克-沃尔克特松-科恩赫特(Dirck Volkertszoon Coornhert,1522-1590 年)。 除了将伊拉斯谟和部分《圣经》翻译成荷兰语外,他还撰写了《沉默的威廉宣言》,该宣言标志着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扬-范-豪特(Jan van Hout,1542-1609 年)是一名诗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语言,他成为了一名语言学家,并参与了这场斗争。
与此同时,中世纪通过口述传统和骑士故事传入宫廷的文学,随着修辞学会的兴起而进入了资产阶级社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 1517 年左右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De Eglantier(《玫瑰蔷薇》,其徽章是象征爱情的花朵)。 当时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都是这个圈子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阿姆斯特洛丹的亨德里兹-劳伦斯松-斯皮格尔(Hendriz Laurenszoon Spiegel,1549-1612 年),他是这个圈子的首领,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是献给他的家乡阿姆斯特洛丹的;还有比他小两岁的同胞罗默-维舍尔(Roemer Visscher),他最喜欢的文体是书信体。剧作家塞缪尔-科斯特(Samuel Coster,1579-1665 年)也曾来过这里,他的剧本《农夫 Teeuwis de boer》(《农夫 Teeuwis》)就是在这里上演的,或许他的古典悲剧《Ithys》也是在这里上演的,该剧被认为是荷兰语创作的第一部古典悲剧。就在此时(1615 年左右),该团体开始出现一些分歧,导致另一个实体 Duytsche 学院的成立。杜伊谢学院同样致力于诗歌和戏剧,同时也致力于用荷兰语进行科学研究(与其他仍用拉丁语授课的大学不同),是塞缪尔-科斯特(Samuel Coster)、皮特-科内利松-胡夫特(Pieter Corneliszoon Hooft,1581-1647 年)和格布兰德-阿迪亚恩松-布雷德罗(Gerbrand Adiaenszoon Bredero,1585-1618 年)的意志和才华的结晶。前者自 1611 年出版歌曲《Emblamata amatoria》以来,一直被视为荷兰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后者则凭借《Geeraerdt van Velsen》(1613 年)颠覆了戏剧规范、后者以其通俗歌曲(《Le Grand Chansonnier bouffon, amoureux et pieux》)一举成名,并先于同时代人在其剧本《Moortje》(1615 年)中表明了反对奴隶制的立场。
然而,如果没有雅各布斯-卡茨(Jacobs Cats,1577-1660 年)--他可以说是 "荷兰之泉"--和约斯特-范登-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1587 年出生于科隆,1679 年卒于阿姆斯特丹--他对荷兰戏剧的影响既可与莫里哀相比,也可与莎士比亚相比),这个充满活力的时期的画卷将是不完整的。尽管弗里斯兰语在16世纪末被完全否定,但他还是将弗里斯兰语提升到了文学语言的地位。最后,让我们以一位哲学家的诞生作为结束,他就是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尽管他于 1677 年在海牙英年早逝,年仅 44 岁,但他仍是该学科的关键人物。尽管他生前不敢出版《伦理学》,而且该书问世后直接被禁,但它仍然是荷兰乃至17世纪最重要的著作,对荷兰以外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衰落与复兴
对独立和征服的渴望与对世界的开放并存,但这也意味着对外部影响(主要是法国影响)的某种渗透性。然而,古典主义的传入在某种程度上寄生于本地作家的创新灵感,因此18世纪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作品,尽管我们应该提到威廉-范-哈伦(Willem van Haren)的史诗《弗里索》(Friso,1741 年)或贝蒂-沃尔夫(Betje Wolff)和阿吉-德肯(Aagje Deken)四手联弹的小说《萨拉-伯格哈特家族史》(Historie van mejuffrouw Sara Burgerhart),后者于 1782 年开创了这一流派。直到本世纪末,随着里恩维斯-费斯(Rhijnvis Feith)的 "感伤主义 "小说《朱莉娅 》(1783 年)的出版,以及德国浪漫主义的逐渐兴起,这一流派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政治问题和其他对抗很快为这一新趋势增添了民族主义色彩,正如扬-弗雷德里克-海尔默斯(Jan Frederik Helmers,1767-1813 年)的诗歌所表明的那样,他的诗歌从温情脉脉(《Nuit》,1788 年)转变为爱国主义(《荷兰民族》,1812 年),尤其是从他开始与其妹夫科内利斯-卢茨(Cornelis Loots,《荷兰语言》(1814 年)的作者)交朋友的那一刻起。最能体现这种转变的人是亨德里克-托伦斯(Hendrik Tollens),他是一位诗人,在《Ceux chez qui coule le sang néerlandais》(写于 1817 年,威廉-比尔德迪克开始在莱顿教授历史的同一年)一书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座城市和这个人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莱顿大学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麦加圣地,比尔德迪克的崇拜者和弟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包括诗人伊萨克-达科斯塔(Isaäc da Costa),他显然是比尔德迪克的继承人。
浪漫主义往往遭到现实主义的迎头痛击。这种尽可能贴近事实的新野心,也包括谴责,最终形成了一部以 "Multatuli"(拉丁语,意为 "我承受了很多")为笔名出版的小说。Max Havelaar》(1860 年)几乎是 Eduard Douwes Dekker 的自传体作品,他在自己出生的房子(该房子现已成为纪念他的博物馆(阿姆斯特丹 Korsjesportsteeg 20 号))中长大后,前往荷属印度群岛,在那里反抗爪哇人民遭受的压迫。这本书从一开始就非常畅销,现在法文版已由巴别出版社出版。同样,雅各布-扬-克雷默(Jacob Jan Cremer,1827-1880 年)在《Frabriekskinderen》(1863 年)中抨击童工。雅克-珀克(1881 年因病去世,年仅 22 岁)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对诗歌规范提出了挑战,他的朋友威利姆-克洛斯(WilliemKloos,1857-1938 年)出版了他的十四行诗。与他同时,阿尔伯特-维尔维、弗雷德里克-范-伊登和赫尔曼-戈特也对传统美学进行了革新,并在De Nieuwe Gids(《新指南》)上发表了他们的散文。
20世纪和21世纪
随着 1910 年 "一代人 "及其刊物《运动》(De Beweging)的问世,诗歌越来越多地转向象征主义,而小说则放弃了现实主义,变得神秘(甚至神秘主义)起来--如小说《De Stille Kracht》(1900 年),路易-库珀勒斯(Louis Couperus)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爪哇岛,就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或者通过描述想象中的过去,将自己代入新浪漫主义(阿瑟-凡-申德尔(Arthur van Schendel)的《玛丽-让娜号》,1903 年)。事实上,那是一个相当富饶的时期:内西奥出版了短篇小说(《De uitvreter》,1911 年),西蒙-维斯特迪克(Simon Vestdijk)的作品成倍增加,格利特-阿赫特伯格(Gerrit Achterberg)在 1931 年完成了他的作品集《Afvaart》......然而,正如评论家门诺-特尔-布拉克(Menno ter Braak)所强调的那样,纳粹的威胁已经存在。 1936 年,他与他人共同成立了一个警戒委员会,四年后,当他的担忧得到证实时,他自杀了。年幼的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展现得栩栩如生,她描述了自己在秘密公寓中的日常生活,直到她被告发并被送往卑尔根-贝尔森,在那里她不到 18 岁就丧生了......。
在这场冲突中,无论是她的生还者还是文学作品,都未能幸免。 现在已不再是顾及读者感受的时代,因此出现了一种被一些人称为 "令人震惊 "的现实主义。杰拉德-雷夫(Gerard Reve)(《第四个男人》)和安娜-布拉曼(Anna Blaman)(《Op leven en dood》)是第一批描写同性恋的作家,他们描写了自己和笔下人物的同性恋。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在一篇关于荷兰文学的文章中也没有放过他的同龄人,他的小说(包括米兰-昆德拉认为是杰作的《达莫克勒斯的黑屋子》)也同样粗俗。至于哈里-穆利什,战争对他来说是一出私密的戏剧,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通敌者。他在一篇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散文(《40/61 事件》)中深入探讨了自己对战争的痴迷,但最重要的是,他凭借小说《天堂的发现》赢得了所有赞誉,成为荷兰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直到 2010 年去世。
对个人身份而非集体身份的追求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困扰作家的问题,在21 世纪仍是如此,包括那些并非在荷兰出生但居住在荷兰的作家,以及由此产生的双重文化或排斥问题。第二个显著变化是读者群的变化,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加富裕,渴望发现新事物。我们现在很幸运,因为译本数量不断增加,我们也能用法语进行这些探索。因此,我们可以继承那些在过去几十年中产生了持久影响的作家的作品,比如海拉-哈斯(Hella S. Haasse)。哈斯(1918-2011 年),从她的小说《Un goût d'amandes amères》到她的短篇小说集《Aloe ferox》;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从他的短篇小说(《Le Matelot sans lèvres》)、长篇小说(《Rituels》、《Le Jour des morts》)或散文(《533 : le livre des jours》、《Venise :作家兼历史学家 Geert Mak(《穿越二十世纪的欧洲之旅》)、令人不安的 Hans Maarten van den Brinck(《重量与尺度:比较》、《水之旅》),以及早熟的 Arnon Grunberg(生于 1971 年,22 岁时出版了经典作品《Lundis bleus》,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重新赢得了法语书商的青睐(《Taches de naissance》、《Des bons gars》)。